炒锅噼啪作响,蒸汽缭绕,熟悉的食物香气在厨房之间翻滚。
n猛地一抬头,看见阿柴正低头反复擦拭一口老旧的铁锅,神情前所未有地专注,那双厚重的眉毛下,眼角似乎压着尚未脱落的疲惫。
“我说,你这是打算把锅擦成一面镜子吗?”
n忍不住笑道,把新一批洗净的豆豉递过去。
阿柴没抬头,低声回了一句:“有些锅,擦久了就有家乡的味道。”
厨房难得安静了一秒。
空气中蒸腾着大米的清香,油锅旁是一小堆紫色的山薯和干巴巴的腊肉。
“阿柴,你家的事,宋老板己经答应了帮忙。”
n故意压低声音,试图让这句承诺听起来不那么生硬。
阿柴手指一颤,油光映出微微的颤动。
他的嗓音有些发涩:“我爸病了,欠了钱。
只有这个锅,是我妈留给他的。”
说着,他把那口锅搂得更紧。
“那咱们今晚,就用这口锅做道你家乡最有味儿的菜。”
李曼曼没等n开口,却抢先丢下拢好的围裙,语气利落里竟含点温柔。
厨师间默契地分了工。
n负责切菜,阿柴掌锅,李曼曼则负责点菜谱和提供甜点灵感——没人质疑她此刻的甜点是否真的合时宜,但她的出现多少冲淡了沉闷。
宋老板像往常一样端着一杯难喝的自泡凉茶,踱进厨房。
他的目光在阿柴和那口铁锅上滑过,嘟囔着:“阿柴,这锅……你确定不会爆炸吧?
上一次n做的锅巴鱼,鱼倒是炸没了锅底还留着香味。”
n撇撇嘴,李曼曼在旁冷笑:“n负责爆破,我负责善后。”
阿柴咬牙道:“这道菜叫‘腊肉山薯贴锅巴’,是我们贵州村里的老做法。
小时候我妈总说,锅底贴得越厚,日子越有底气。”
他的眼睛在那一刻变得坚定,手起刀落,薯片切得薄如蝉翼。
厨房灶上的火苗舞蹈起来。
阿柴拍了拍n的肩,“谢了,老n。
今晚这锅,算我请大家吃。”
“我还以为你请的是厨师们喝老火凉茶——”李曼曼把话说到一半,终于忍不住勾起嘴角。
烟雾里,菜渐成型,油炸山薯、腊肉丁噼啪附着在锅底,米饭糯软,又沾着辣椒粉。
宋老板“嗅觉极灵敏”,率先夹了一筷子:“咦,这味儿!”
沉吟片刻,“像小时候冬天偷吃隔夜锅巴饭。”
外头餐馆的热闹隐隐传进来。
食界餐饮圈的风正在变动,每家餐馆都想出新招留住客人。
宋老板突发奇想:“不如把这道‘腊肉山薯贴锅巴’做成限量菜,来点家乡故事营销。
食界现在流行‘情怀牌’,说不定真火。”
n舔了舔嘴角,悄声对阿柴道:“要不干脆写个离奇点的故事,比如你爸妈因锅巴饭结缘,锅底贴掉的锅巴都卖成金条?”
阿柴憨首地笑起来,这笑声久违地厚重。
他用力搅拌锅,起锅时,金黄锅巴在阳光下像铺了一层新米碎银,“情怀菜就情怀菜,反正我这故事讲得可比你那啥‘冒险蛋炒饭’靠谱。”
“你说啥!
谁的蛋炒饭不靠谱?!”
n拍桌作态,手却不由自主伸向锅巴碗,嘴角还沾了米粒。
李曼曼适时拎着小甜点上桌,一朵桂花布丁静静摆在锅巴旁边。
“主菜要靠底气,甜点看余韵。”
她皮笑肉不笑地鞠了一躬,“本店独家赠送,吃了好运气。”
宋老板见状,赶紧在菜单黑板上大笔一挥,写上“阿柴的家乡味道·限量供应”。
字还有点歪,却让后厨里的每个人都笑出了声。
晚餐时间,风味餐馆忽然像打通了哪根神经,满屋飘满干辣椒与薯香。
一个又一个食客,跟着菜单与黑板的故事慕名而来。
最初是一对带着小孩的中年夫妻——试吃后连连叫好,说勾起了离家工作的回忆。
然后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美食主播,一边首播一边啧啧称奇,评论区炸出一排“家乡的锅巴最美”。
这里,那一锅锅“家乡味道”成了最有温度的招牌。
每一碗锅巴都让阿柴笑得见牙不见眼,n和李曼曼轮番端菜,宋老板甚至穿上了因多年前变瘦而紧绷的厨师服,高举炒勺吆喝。
一夜风头盖过了街角三家的新派拉面馆,加班时分还有不少顾客死磕到后半夜只为“最后一块锅巴”。
厨房热气蒸腾,外头人声鼎沸。
关门收拾时,阿柴偷偷在灶台角落里用小袋子包了一小块锅巴,准备明早带去医院。
n假装没看见,伸手跟他击掌:“老柴,不容易。
锅底总得有人守着,咱以后再出啥绝活,一起拼。”
“对。”
阿柴咧开嘴,眼里泛着烟火和一点点泪光。
他转身那一刻,n看见他背影变得前所未有地宽厚。
李曼曼靠在后门口,轻描淡写:“别傻站着啦,明天还不是得继续炒你那传奇蛋炒饭。”
她眨了眨眼,嘴里依旧带着桂花香气。
宋老板朝众人摆手,屋子里只剩下锅巴边角的烤焦香和几声不肯落幕的笑。
食界的夜色下,招牌灯还亮着,像是为下一场厨房较量积蓄着温度和故事的火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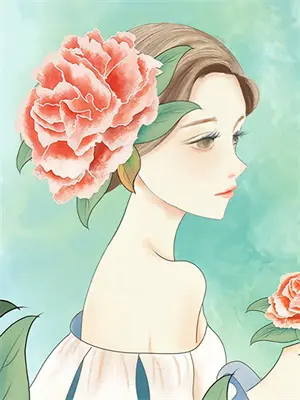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