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寄出去后,我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。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高强度的勤工俭学中,用忙碌麻痹自己,也用知识的积累武装自己。
期中考试,我的成绩稳居年级前列,甚至数学和物理拿到了单科第一。班主任在班会上特意表扬了我,说我“家境困难但志存高远,是同学们的榜样”。
同学们看我的眼神,多了几分敬佩,少了几分最初的探究和疏离。我知道,在这个以成绩论英雄的环境里,我初步赢得了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食堂的工作我也干得越发熟练,甚至和掌勺的师傅混了个脸熟,偶尔他还会给我多打一勺没什么油水的菜。生活依旧清苦,但能看到自己凭借努力一点点改变处境,心里是踏实的。
然而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一个周六的下午,我正在宿舍里埋头刷题,室友探头进来:“陈建华,楼下有人找,说是你家里人。”
家里人?
我心里咯噔一下,第一个念头是母亲或者弟妹找来了。他们怎么会找到学校来?是那封信激怒了他们吗?
我放下笔,深吸一口气,走下宿舍楼。
站在宿舍楼门口树下的,不是母亲,也不是弟妹,而是两个我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——我的大伯陈富贵和小叔陈满仓。
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旧中山装,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不耐烦,正皱着眉头打量着光鲜的校园,眼神里混杂着些许羡慕和更多的不以为然。
“大伯,小叔。”我走过去,语气平淡地打招呼。前世,父亲瘫痪后,这两位至亲亲戚可是躲得远远的,生怕被沾上,别说帮忙,连看望都寥寥无几。如今主动找来,必定无事不登三宝殿。
大伯陈富贵看到我,上下打量了几眼,哼了一声:“哟,大学生回来了?架子不小啊,还得我们两个长辈来找你。”
小叔陈满仓在一旁帮腔,语气带着指责:“建国,不是小叔说你!你爹瘫在床上,你妈病歪歪的,你倒好,跑到城里享清福来了!像话吗?”
果然,兴师问罪来了。
我没有被他们的气势吓住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:“大伯,小叔,你们来找我,有什么事?”
“什么事?”大伯眼睛一瞪,“你还有脸问?你妈都快哭死了!你弟弟妹妹学费交不上,家里都快断顿了!你倒好,在外面吃香喝辣,一分钱都不往家里寄!你的良心被狗吃了?”
他的声音很大,引得路过的学生纷纷侧目。
我感受到那些目光,脸上有些发烫,但更多的是心冷。他们根本不问青红皂白,就给我定了罪。
“大伯,”我打断他的咆哮,“我怎么就吃香喝辣了?我上学靠的是助学贷款,以后要还的。吃饭靠的是在学校食堂打工,勉强糊口。你们看我,像吃香喝辣的样子吗?”
我扯了扯自己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子。
小叔撇撇嘴:“谁知道你是不是把钱藏起来了?反正你没往家里拿钱就是你不孝!”
“就是!”大伯接过话头,“我们老陈家没你这种不孝子孙!今天我们来,就是告诉你,要么,立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,伺候你爹,挣钱养家!要么,你就每个月按时往家里寄钱!不然,我们就去找你们学校领导,让大家都评评理,看看你这种不孝子还配不配读书!”
图穷匕见。
他们不是来关心我的,是来施压的,用长辈的身份,用孝道的大棒,甚至用闹到学校相威胁,逼我就范。
前世,我或许会被这种阵仗吓住,会因为害怕失去读书的机会而妥协。
但现在的我,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少年。
我看着他们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,看着他们眼中毫不掩饰的自私和算计,心中最后一点对亲情的期待也彻底湮灭。
“大伯,小叔,”我的声音冷了下来,“首先,我父亲的治疗和赡养,是你们作为兄弟的责任,还是我这个未成年儿子的责任?你们作为亲兄弟,在我家遭难时,出了多少钱?出了多少力?”
两人脸色一变,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反击,还把矛头指向了他们。
“你……你胡说什么!我们也有家要养!”大伯有些气急败坏。
“我也有学要上!”我寸步不让,“其次,我靠贷款和打工读书,合理合法。你们要去学校领导那里闹,尽管去。正好,我也想让领导评评理,看看逼一个靠助学贷款读书的未成年孩子放弃学业去养家,到底合不合法,合不合理!”
我的态度强硬,语气斩钉截铁。
大伯和小叔被我的气势镇住了,他们大概以为我还是那个在家里沉默寡言、逆来顺受的大侄子。
“你……你个混账东西!”小叔指着我的鼻子骂。
“小叔,”我冷冷地看着他,“骂人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你们真是为了我家好,应该帮着去催工伤赔偿,或者帮着我妈去申请政府救济,而不是来这里逼我一个孩子。”
我顿了顿,下了逐客令:“我还要学习,没别的事,你们请回吧。”
说完,我不再理会他们铁青的脸色和后续可能更难听的咒骂,转身径直回了宿舍楼。
我知道,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结束。他们回去后,肯定会添油加醋地在村里和家里败坏我的名声。
但那又怎样?
我已经不在乎了。
流言蜚语杀不死我,但妥协和退让,会。
这一次,我绝不会后退半步。我的战场在课堂,在书本,在通往未来的这条独木桥上。
谁想把我拉下来,我就算拼个头破血流,也要把他们踹开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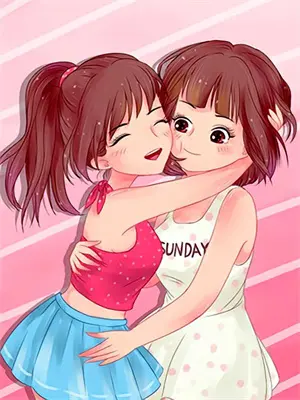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